|
Regarding Chen Weixi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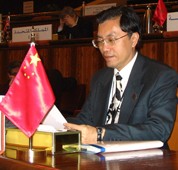 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o inform you about the recent appointment of one of our GW77ers--CHEN Weixiong as chief of Branch, Counter-Terrorism Committee, Executive Directorate (UNCTED)in UN New York(反恐执行局执行主任). Please join me in congratulating him on his new assignment as a high-ranking UN official (D-1) entrusted with matters of serious concern to us all, and to our fellows in USA in particular. Hi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s widely
acknowledged, both officially and in private. It is the result of his persevering efforts through all these years that are crowned with such an honour. This is also an honour for us. Let's share the joy on this occasion and hope his diplomatic career to bring about even greater success in future.(Li Pei) 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o inform you about the recent appointment of one of our GW77ers--CHEN Weixiong as chief of Branch, Counter-Terrorism Committee, Executive Directorate (UNCTED)in UN New York(反恐执行局执行主任). Please join me in congratulating him on his new assignment as a high-ranking UN official (D-1) entrusted with matters of serious concern to us all, and to our fellows in USA in particular. Hi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s widely
acknowledged, both officially and in private. It is the result of his persevering efforts through all these years that are crowned with such an honour. This is also an honour for us. Let's share the joy on this occasion and hope his diplomatic career to bring about even greater success in future.(Li Pei)
--------------------------------------------------------------------------------
《耍一把外交一个现役中国外交官的自述》
陈伟雄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6月版
一位现役中国外交官讲述联合国里的轶闻趣事
在电视荧屏上,我们经常能看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那标志性的建筑,看到各国外交官在环形大厅内开会和发言
我们对联合国的印象大抵就是如此。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曾在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五年多的陈伟雄,在《耍一把外交一个现役中国外交官的自述》一书中,披露其在联合国里亲历亲闻的一些轶闻趣事,也算是让世人稍稍窥到一点门道吧。上海《解放日报》今天摘登该书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无可奉告不再盛行
以往,一句无可奉告的外交辞令,便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打发任何人。现在,这句外交辞令已经不吃香了。要想用这句外交辞令敷衍了事是大大的不得人心!
如在联合国,每天中午都由秘书长的发言人在大楼二层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他需要当场回答新闻界和各国外交官围绕国际和地区重大事件提出的各类问题。对于当时无法答复的问题,发言人很少简单地说一句无可奉告。他通常会改用另一种外交辞令,如你提到的问题确实非常重要,我要去查一下。这叫虚晃一枪。如果下次无人问,也就不了了之了。
秘书长是联合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是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推荐并由联合国大会核准而产生的。对外界而言,秘书长应该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全才,嘴上就算吐不出象牙,也万万不能吐出无可奉告四个字。有时,为了照顾各方关切和避免节外生枝,秘书长本人也不得不借助外交辞令,如用对某某事情的进展表示赞赏或欢迎来代替明确表示支持。又如称某某行动无助于什么什么来代替明确表示反对。当他觉得没必要指名道姓批评某个国家政府或某一武装派别时,他便会改用敦促有关各方执行联合国的决议等笼统提法。这种外交辞令既点到为止,又不失面子,联合国会员国政府可以根据有关各方来对号入座,也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2002年7月,秘书长就联合国核查伊拉克武器事宜与伊拉克外长进行了第三轮会谈。秘书长会后仅对外界简要表示,该轮会谈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没有预期的多。这种不痛不痒的辞令,对各方都有交待,也令当时磨刀霍霍的美国政府暂时找不到对伊拉克下手的借口。
负责核查和销毁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联合国监核会主席布利克斯,受命于危难之时,于2002年11月下旬率团赶赴伊拉克亲自指挥现场的核查工作。两周的核查过去了,各方都非常关注核查结果。
面对围成好几圈的记者,说深说浅都会为伊拉克和布利克斯本人带来最严重的后果。这时,布利克斯没有简单地用无可奉告来搪塞,而是巧妙地答道:联合国核查人员查了两周,未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这不等于说伊拉克就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说掌握了伊拉克实质性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大量情报,但美国却一直未能向监核会交来过任何一份资料。他这种应对既清楚,又模糊,为记者们留下了各自发挥的报道空间。
他的这种外交技巧,使我联想到在我国许多医院,负责肺部透视的医生通常在病人诊断单上手脚麻利地盖上一个未见异常的红印章。这其实也应该算是一种外交辞令。这个未见异常的说法,既可以理解为你的肺部是否有病变,我的X光机看不出来,也可以理解为这并不意味着我的X光机看不出来,你的肺部就没有病灶。
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
长期以来,在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五个常任理事国配备的人员最多。联合国有一本各国外交官的花名册。这本蓝色封面的花名册每年更新一次,免费向所有代表团提供。在这本花名册上,有真名实姓的美国外交官有110~120名,俄罗斯有80~90名,英国、法国和我国都在50~60名之间。这支庞大的外交官队伍可谓藏龙卧虎、人才济济。高级别的官员俯拾即是,而一般级别的官员充其量只能算办事员而已。
如目前在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参赞级以上的外交官便有20名。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都是副部长以上级别的大使。我国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王英凡大使赴任之前就是外交部副部长。这些大人物任何时候都有一点脾气,但他们在任何时候说话却能管用!当然,五常另外还有从事特殊工种的工作人员。这种不在花名册之内的人员总数就不得而知了。
五个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大楼二层有一间专门的磋商室,房号为C座209。这间磋商室八九平方米。每逢世界上发生大事急事,五常各级官员的磋商便会跟着时代的脉搏,变得频繁起来。这时,该磋商室就犹如急诊室,格外引人注目。一些媒体的记者削尖了脑袋,设法混进大楼内,将摄像机直接架在磋商室的出口处,同步猎取五国大使的动静。一些文字记者则各有绝招,手握微型数码录音机,尾随五国大使或其助手,见缝插针地偷偷采访第一手资料。有时,外交官们一不留神,就陷进了记者们布下的天罗地网。
五常的这种磋商通常由其中一国担任协调员,按中、美、俄、英、法的次序轮流坐庄,每次任期三个月。由于安理会的活儿常常十万火急,五常经常需要及时进行短平快的碰头。只要一家有要求,五常磋商便会随时在该磋商室举行。大家一般都会开门见山,闲话少说,直奔主题。能够谈出共识,就按此贯彻落实,暂时谈不拢,也不必心急上火,下回有话好好说就是了。
安理会一些重大的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通常由五常事先磋商并达成一定共识之后,才拿到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考虑到五常的特殊工作需要,联合国后勤处在磋商室内免费提供四五大扎冰镇水。有时,一场磋商下来,所有的玻璃杯都见了底,可见讨论之激烈。
在五常当中,我国首都离纽约的路程最远,旅行费用最高。每次,我国外长前往纽约开会,都是匆匆而去,匆匆而回,有时甚至只能在纽约呆上一天,吃上一顿午餐。有一次,有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开玩笑地说,要折算起来,中国外长在纽约的午餐是五常外长中最昂贵的!
逃票是一种解脱
安理会的决议通常需要经过各个理事国大使举手表决通过,少数决议在事先征得大家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鼓掌方式通过。这只是一般的规矩。如果理事国对决议草案表示不满,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可以举手表示弃权。但也有打破常规的,即以逃票方式解脱自己。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天下午,安理会紧急讨论朝鲜局势,结果在当时苏联有意或无意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北朝鲜的武装进攻是对和平的破坏,要求它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将军队撤回到三八线。
这种不参加表决的方式有很大的好处:即你不知道我是哪个态度,我也表明了我的那个态度!
说来有趣,后来将这种规矩学得最快的竟然是我国代表团。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我国凡事以美苏划线,认为联合国安理会部署的维和行动是美苏争霸行径,不能支持,也不便弃权。因此,每当安理会就维和行动进行表决时,我国代表团都会奉示不参加投票。结果,每次投票结束后,都有许多理事国的大使前来打探我国究竟持什么态度?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我国调整了立场。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会内的投票态度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对许多不能赞成的决议改为弃权。逃票大使的美名去了,却又得了一个弃权大使的尊称。
1999年,在安理会关于伊拉克问题的一次投票中,为了摆脱进退维谷,法国也来了一个不参加投票。事后,法国人还专门将我国代表团当作祖师爷来感谢,认为大使逃票与学生逃学不一样,是一种真正的外交艺术!
听会功夫
在联合国工作的外交官需要具有几个基本要素,其中之一是听会的功夫。初来乍到的人不知道深浅,听会记录都是认认真真的,生怕有丝毫闪失。但对于在联合国多边领域工作多年的外交官来说,听会却是一门有趣的学问,人坐在座位上,时间一长,便可以听出不少门道和味道来。
听会是讲究窍门的,据说掌握了便能事半功倍,如能听得懂,整理会议记录亦会得心应手。
最通常的听法是掐头去尾。一般发言稿的开头部分无非是感谢某某主席主持会议有序,前面某某大使的发言如何如何不错。这些都是客套话。结尾部分无非是复述稿子提到过的核心内容,或以一些口号表达美好的愿望等等。听众大可听而忽之,因公因私迟到或早退一点也影响不大。
最轻松的听法是左耳进、右耳出。在联合国的各个论坛,许多国家的发言只是老生常谈,并无新意,至多只是为了体现该国参加了某个问题的讨论而已。有一些国家对某某问题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还未开口已能猜出八九不离十。对于这类发言,听众可以采取印象派方式处理,知道某某国家发过言便行了。
最实惠的听法是一心多用,边听边想自己的事儿。各国在联合国会议厅内都有自己相应的位置。为了尊重别人的发言,也是为了例行公事,许多时候各国代表必须到现场坐会。虽然会议讨论的可能只是一般性问题,但如果届时连某某国家的一般级别代表都不在场内听会,亦会引起外界不一般的猜测。这时,坐会的外交官应该过好每一分钟,充分利用这段时间琢磨自己的事儿,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儿女情长。只要双眼不要发呆,脑袋不要后歪,两手不要托腮,不管你如何异想天开,也不会有人来责怪。
最健康的听法是时坐时立时走动。坐会需要耐力和听力。在半米见方的席位上长时间不动,几年下来不闹出点颈椎或腰椎病就算是上帝保佑了。许多懂行的代表在联合国大楼的会场内听会,都会注意自身保健。好在联合国的会议没有不许离场,必须鼓掌等硬性规定,代表们坐累了,听烦了,都可以离开座位,在会场后站立一会,或在会场外的走廊内抽几口名牌香烟,甚至到室外吸几口新鲜空气。
在多边领域的会场内,耳尖手快的行家里手都是通过长年累月的大量会务实践,才修炼成精的。
发言要抢点
联合国是一个重要的多边讲坛,与会代表们都是有备而来的,即:带着脑袋、嘴巴、耳朵和双手。通常,在国际会议上发言需要预先向会议秘书长报名,也可以在会场内临时举牌或举手发言。如果没有特别的规则,通常是先来后到,挨个排队。如果需要提前夹塞儿,就必须找到一个国家更换发言时段。争取一个好的发言时段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就犹如掌勺的厨师需要掌握好开锅的时间一样。
联合国的会议通常在上午10时或下午3时开会。由于人多事杂,重要的贵宾和打杂的助手往往都难以准时与会,因此,有四个时间段是兵家大忌。如上午第一个发言的代表大多是对椅弹琴。午餐前最后一个发言的代表则会目睹人们纷纷离席就餐。下午第一个发言的代表势必会同时听到台下许多回声原来是有人在打饱嗝。晚上最后一个发言的代表则会是月亮走,我也走,我送自己到床头!
2001年8月,我赴南非德班参加联合国反对种族歧视大会。当时,100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都报名发言,东道主不得不安排夜会。结果,各国代表团都设法争取白天最好的发言时段。
有一天恰好轮到新加坡代表团在夜会上作最后发言。新加坡代表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向下一看,真是惨不忍睹:偌大的一个会场内只剩下主席和寥寥几名打着哈欠的工作人员。新加坡代表在发言时,故意改动了发言稿惯用的一句开场白。他讽刺地说道:尊敬的摄像机镜头,尊敬的桌子们、椅子们,新加坡代表团想借此机会向你们致意,感谢你们参加这次重要的夜会!
东道国对此大为尴尬,也无可奈何。
午睡要抢地
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对于来自五湖四海和不同时区的各国代表来说,参加一次联合国会议,其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是用来打盹儿的。
联合国的会议通常采用上午10时至下午1时,下午3时至6时的时段。我在联合国大楼参加会议时,发现其他国家的与会代表也有中午打盹儿的需要。这恐怕是人类的共性,而不单是中国制造。在联合国大楼内找一块中午小憩的地方,说容易也容易,说困难也困难。
如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内,设有沙发和椅子的地方主要包括二楼的代表会客厅和几个开放性的小会客厅、一楼的哈马舍尔德图书馆和普通餐厅、二楼的过道走廊、安理会磋商室外的休息室、地下一层的网吧区、大楼外靠东河的露天便道等。这些休息的地方免费供大家各取所需,实行的是男女平等、先来后到的规则。
每到中午,就会看到休会或用餐后的各国代表和联合国职员争先恐后地抢占这些战略要地。大家午休的方式也是千姿百态的。既有东倒西歪、鼾声如雷的,也有头戴耳机、闭目养神的,倒从来没有看见有人围坐在一起敲三家的。
如何在联合国抢占午休地盘,还真的成了一项有趣的研究课题。前两年担任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阿兰·德雅梅大使还专门对这个问题做过研究,并写出一本名为《睡在联合国》的书。
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这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原来在联合国大楼内都有各自专用的会议室兼休息室。据我国外交老前辈说,我国专用的会议室较小,也没有窗户,通风不好,后来干脆退掉了。现在,只有英国和法国仍保留着自己的地盘。
在联合国大楼二层,还有一间五个常任理事国共用的磋商室,平时都是不上锁的。不知道五国是不是早已有了君子协定,我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五年多期间,从来都未发现有其他四个国家的战略伙伴中午在这个战略要塞做过战略休整。
(作者:陈伟雄)
在联合国咬文嚼字
陈伟雄
《耍一把外交》的作者系职业外交官。从非洲小国塞拉利昂到超级大国美国,都曾是他出使的范围。在五光十色的外交舞台上,他既为重要的大腕们跑过龙套,也曾自己亲自披挂上阵。在本书中,他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披露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所经历的台前幕后的诸多轶事。这里摘录的主要是他在联合国的与语言和谈判相关的有趣经历。
天书与卖拐
安理会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政治机构,安理会的决议可以带有强制性。因此,安理会各个理事国在草拟决议时,都十分注重案文的措词。在多边领域磋商文件其实是一次多人参与的国际游戏。由于各国代表立场不同、关切不同、要求不同、水平不同、理解不同、性格不同、语言不同,玩这种游戏时是非常费时费力的。许多时候,磋商一项巴掌大的声明稿就犹如一场上甘岭战役似的,各方寸土必争,围绕一个小字眼争得面红耳赤。到最后,一项决议便是各方妥协的产物,是由你一言我一语的外交辞令拼凑而成的,不但语法狗屁不通,而且用词怪僻无比,无法破译。我国前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学贤大使就在一次安理会上干脆将这种决议戏称为天书。
有一次,我参加安理会一项决议草案的专家磋商。这项草案是谴责当时某个法语非洲国家的叛军违反《和平协议》,对平民百姓实施了一系列的暴行。大家都希望在其中的一段话中加入强烈要求当事方遵守《和平协议》的内容。
按照中文的习惯,敦促(urge)这个严厉措词是非常合适的,因此,我要求使用这个措词。但英国代表却认为,在英语词汇中,使用call on(呼吁)比敦促更严厉,希望采用呼吁的说法。而美国代表则认为,在美式英语中,demand(要求)就是一个严厉的措词,用在彼处是最合适不过了。法国和俄罗斯又根据各自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的措词。结果,直到日落西山,大家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决定分别连夜请示各自首都,由它们定夺。
又有一次,是在联合国大会讨论财政预算问题的场合。当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们对联合国财政预算报告中未能增加对发展领域的投入表示不满。在讨论联大决议草案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不赞成案文含有肯定这个报告的措词,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急于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于是,大家就什么字眼带有肯定意思,什么措词只有中性解释等展开了大辩论,有雄辩的,有狡辩的,有申辩的,你来我往地拉了半天锯。发展中国家甚至对案文中有一句提到注意到这个财政预算报告的说法亦不放过。本来注意到这个措词的英语既可以用take note of,也可以用note,但发展中国家就是不轻易放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指出,take note of的说法在阿拉伯语中仍然带有肯定的意思,只同意采用note。
在场的西方国家代表没有几个懂得阿拉伯语的,面对人多势众的发展中国家代表,最后只好夹起尾巴,败下阵来。
还有一次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专家磋商一项决议草案。当时,大家对于用什么措词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以俄罗斯为领导的独联体维和部队的作用非常在意,在磋商中还较起了真儿。
俄罗斯的代表坚持要用赞赏(appreciate),而美国、英国和法国则各有考虑,提出了其他同义词,如改用欢迎(welcome)、承认(acknowledge)、肯定(recognize)或满意地注意到(note with satisfaction)等。美、英、法三国专家分别旁征博引、你唱我和,设法自圆其说。绕来绕去,连我这个深受中庸之道影响的专家到最后都被他们绕糊涂了。我当时甚至觉得,要论积极评论的程度,赞赏这个词是最不合适的,其他任何一个词似乎都要比赞赏这个词积极得多!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国春节晚会上,有一个名叫卖拐的小品深受观众喜欢。其实,小品中卖方使用的小伎俩在国际大场面上早已司空见惯。在谈判桌上,谁的脑袋缺一根弦,谁就会中人圈套。
由于起草安理会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大都需要参照以前已获通过的文本措词,有时甚至只需要照葫芦画瓢,因此,大家每次都非常重视文件的调门。有了前面文件的第一胎,后面需要多胎生产的文件就自然顺利多了。难怪每个国家的大使和专家在玩此类文字游戏中,都会争个你死我活。
C座209
五个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大楼二层有一间专门的磋商室,房号为C座209。这间磋商室八九平方米。每逢世界上发生大事急事,五常各级官员的磋商便会跟着时代的脉搏,变得频繁无比。这时,该磋商室就犹如急诊室,格外引人注目。一些媒体的记者削尖了脑袋,设法混进大楼内,将摄像机直接架在磋商室的出口处,同步猎取五国大使的动静。一些文字记者则各有绝招,手握微型数码录音机,尾随五国大使及其助手,见缝插针地偷偷搜寻第一手资料。有时,外交官们一不留神,就陷进了记者们布下的天罗地网。
五常的这种磋商通常由其中一国担任协调员,按中、美、俄、英、法的次序轮流坐庄,每国任期三个月。由于安理会的活儿常常十万火急,五常经常需要及时进行短平快的碰头。只要一家有要求,五常磋商便会随时在该磋商室举行。大家一般都会开门见山,闲话少说,直奔主题。能够谈出共识,就按此贯彻落实;暂时谈不拢,也不必心急上火,下回再继续扯淡好了。
安理会一些重大的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通常由五常事先磋商并达成一定共识之后,才拿到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考虑到五常的特殊工作需要,联合国后勤处在磋商室内免费提供四五大扎冰镇水。有时,一场磋商下来,所有的玻璃杯都见了底,可见讨论之激烈。
在五常当中,我国首都离纽约的路程最远,旅行费用最高。每次,我国外长前往纽约开会,都是匆匆而去,匆匆而回,有时甚至只能在纽约呆上一天,吃上一顿午餐。有一次,有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开玩笑地说:要折算起来,中国外长在纽约的午餐是五常外长中最昂贵的!
不开口也是艺术
安理会的议事规则中,有一条合法不合理的规定,即安理会以什么方式开会,全由安理会的理事国自定。这就是说,安理会想怎么开会就怎么开会,想让谁参加就让谁参加,不想让谁开口就不让谁开口。这种见怪不怪的事情,确实让局外人愤愤不平。
有一次,安理会审议西撒哈拉问题。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向安理会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四种设想。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对这四种设想有不同看法,而阿尔及利亚、西撒人阵、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等当事方亦对这四种设想存在严重分歧。
考虑到各方立场短时间内难以弥合,为了避免大家在公开会议上彼此指责而破坏气氛,大家一商量,决定安理会开会时只举手通过决议,而不安排任何当事方入席和发言。安理会的会议只开了五分钟,西撒问题的当事各方在旁听席上还未坐稳,就散会了。结果,发言的机会没有捞着,问题也丝毫没有解决,大家却捎回去一肚子牢骚。
当然,也有例外的做法,即自己主动要求放弃发言权的。如1991年8月8日,安理会决定同时向大会推荐接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加入联合国。当时,南北两个朝鲜都担心安理会有诈,在接纳问题上厚此薄彼,因此,都坚持要求安理会在同一项决议内,同时解决两个朝鲜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为了防止挑起口水战,两个申请国都主动放弃在会上发言的机会,其他理事国的代表因此亦决定不开金口。结果,在推荐两个新会员国的大喜日子里,没有听到任何理事国发出任何声音。
事后,有人说,朝鲜半岛从来就没有寻常的问题,因此,只能用不寻常的眼光去看待,用不寻常的办法去解决。
啼笑皆非的互译
我周围一些同事有很好的语言功底,他们曾出色地完成了许多重要的翻译任务。但我也听到过一个英雄败走麦城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英文造诣很深的男译员在餐桌上为一位领导当翻译。那位领导三杯下肚,便漫无边际地与外宾扯了起来。在谈到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位领导脱口说了一句歇后语:这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吗?
男译员立即译成:It is as clear as crystal。(注:这是英语惯用法,用像水晶一样清澈来比喻事件的来龙去脉极其明白的意思。)
正当这位译员为自己高超的互译技巧而沾沾自喜的时候,那位领导没事找事儿,接着问外宾:你们国家有豆腐吗?
男译员一愣,只好硬着头皮译下去。他用英文译道:Do you produce crystal in your country?(注: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国家有水晶吗?)外宾这时也来了精神,十分干脆地回答说:Yes。
男译员明知大事不妙,但只好照实译为中文:有啊!
谁知那位领导却更来劲了,追问道:是南豆腐,还是北豆腐?
这时,男译员才知道,自己砸锅的时候终于到了!
还有一次,一个美国代表团在谈判中使用了自带的译员。这名译员原来在北京学习过几年,中文说得非常溜。当美方团长用英文说到中国是一个大国时,这位译员立即将大(big)这个字顺口译成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
事后,我问他为何如此译法时,只听他得意地说,他在北京学习时,发现中国人嘴上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他的这种翻译技巧的确令我大开眼界!
当然,我方译员临场应变的例子亦比比皆是。有一次,我陪同一个外国代表团到北京近郊农村参观。当时,该村一村民在介绍情况时,谈到绿色农作物生长已很少用尿素了。我方一名年轻译员当时大概不知道如何英译尿素这个词,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用汉语音译成niaosu。幸亏客人当中无一是庄稼人,让翻译给蒙混过关了。
最近,我发现英语版的《中国日报》亦将汉语中的小康一词直接音译成xiaokang。我想,照这样下去,翻译这活儿,俺就算没有金刚钻,今后也一定会越来越好耍的。
(摘自《耍一把外交一个现役中国外交官的自述》陈伟雄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6月版16.00元)
|

